一場為期4年的對賭合約,牽扯出了一起高達5375萬元個人所得退稅案。
納稅人王某在2016年獲得了一筆來自A公司的價值5.75億元的融資,并以20%的個人所得稅率繳納了1.14億元的稅款。不料對賭失敗,王某向投資方A公司補償了價值2.69億元的股票。
王某以“業績補償仍屬股轉交易”為由申請退稅,卻被稅務局告知,股權轉讓系獨立的交易行為,股票完成登記時即完成了股權轉讓,后續對賭失敗的業績補償行為無法成為退稅的理由。
王某就此提起訴訟,法院在表達對王某的同情和對現行稅法調整的建議的同時,在稅收嚴格法定原則指引下,并未支持王某的退稅請求。王某稱,本案如不予退稅,涉案股權交易的實際稅率將高達37.84%。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王陽認為,稅收法定原則是我國的稅收收入與稅收秩序的基本原則。因缺乏相應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規定,以業績補償申請退稅難以獲得法律支持。為避免出現轉讓股權自然人稅負畸高的情況,股權交易的雙方可在商事交易框架下,采取優化合同條款,選擇合理盈利預測等方式予以規避。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認為,以“實質課稅”來看待對賭協議的應稅金額更具有合理性。立法機關及司法機關可以通過對法律的解釋與補充,以應對多變商事交易中稅法的需求,同時稅務部門應積極調整相關政策,為經濟新業態提供更合理更確定的稅收規則。
時間還要拉回到2015年。
2015年起,A公司先后與王某等人簽訂了《購買資產協議》《業績承諾補償協議》《利潤預測補償協議》等系列協議,計劃以支付現金加發行股份的方式為目標公司B公司融資,約定B公司須在2016年至2019年完成約定的凈利潤目標。
在這場對賭協議中雙方約定,對于王某等人所持有B公司100%的股權,A公司以發行股份的方式購買股權對價的56.5%,以現金方式購買剩余股權對價的43.5%。隨后,A公司依照滿足利潤預測提前支付了全部對價,先后向王某支付現金2.5億元,定向發股3320萬股(約合3.25億元),股票已實際登記至王某名下。2017年,王某依照現金收入與股權收入向稅務局繳納稅款1.14億元。
由于B公司并未如約完成2018年、2019年的凈利潤目標,王某先后以股票形式向A公司進行補償,共計補償了2745萬股股票(約合2.69億元)。
2022年10月,王某認為其股權轉讓交易多申報和繳納個人所得稅5375元,以對賭失敗補償股份導致股權轉讓所得利益減少為由,向稅務局申請退還。
稅務局稱,依據現有法律規定,當股份登記至王某名下時,王某即完成了該筆股權轉讓交易。該交易中王某獲得股票對價3.25億元,加之其獲得的2.5億元現金收入,在減去500萬元的投資成本之外,應納稅所得額應為5.7億元,依照20%的個人所得稅率計算,王某應納稅額為1.14億元,作出不予退稅決定。
此外,稅務局認為,王某所稱1.14億元的個人所得稅稅款屬于預繳性質并不成立。稅法上規定的“預繳”需由法律明確規定,目前個人所得稅法中明確規定,采用預繳加匯算清繳模式的個人所得稅,僅限于居民個人取得綜合所得或經營所得,股轉所得不適用預繳制,無法通過預繳加匯算清繳模式來重新核定應納稅額。
王某稱,本案如不予退稅,涉案股權交易的實際稅率將高達37.84%。
對賭協議中,“估值調整機制”繞不開對投融資雙方的業績補償,由于目標公司是否實現業績目標處于一種不確定性,雙方通過約定“或有對價”,以股權回購、金錢補償來調整未來目標公司的估值。
根據“或有對價”的支付時間,可以將對賭協議劃分為正向對賭和反向對賭。正向對賭是指投資方先向融資方支付一個基礎對價,當目標公司完成對賭目標時,投資方再向融資方追加支付交易對價。反向對賭是指投資方于交易達成時支付交易的總價款,當目標公司未完成對賭目標時,則融資方須向投資方支付一定的補償。
依據案情描述可知,王某與A公司之間為反向對賭。A公司實際支付了全部融資款,在業績未完成時,A公司以2元總價回購了王某所持股份,實際上是王某對A公司作出的業績補償。
反向對賭中,業績補償是否可以折抵應稅金額呢?
目前我國沒有對該項稅務處理的明文規定,在實務中,不同地區作出了不同的處理決定。大部分地區依據“形式課稅”原則,將對賭交易視為“兩次交易”,未將業績補償作為應稅所得核減金額。比如本案二審法院說理認為,王某股權轉讓的實際獲益減少,系在納稅義務發生后,是基于相應經濟目的履行另行達成的協議約定,不對交易價格產生影響。
當然,也有部分地區展開了積極有益的嘗試與實踐。在廣東、海南等地,地方稅務機關將對賭交易視為“一次交易”,支持在對賭失敗后,對股權對價調低部分適度退稅。
王陽告訴記者,依據稅收法定原則,“形式課稅”是我國的稅收收入與稅收秩序的強力保障,對賭協議往往是長時線商業交易,將其視為“一次交易”在整體交易完成后才征稅,有可能會造成我國稅款的流失,也變相為投機逃稅留下了缺口。這也是為什么本案中稅務機關和法院都予以拒絕的內在考量。
王陽提到,對賭協議作為激勵企業發展的有力機制,不論是稅務機關,還是立法機關,都應考慮股權投資及相應的對賭協議的特殊性。建議有關部門可以在對股權交易中的對賭協議進行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出臺針對對賭協議的特殊稅務處理政策,將一定時限內(比如說三年或者五年)的股權交易視為“一次交易”,分批征稅、分步征稅,最終匯算清繳。這樣既可以保證國家稅款不予流失,又可以充分保護納稅人的利益,更有利我國的股權投資、股權交易的發展。
同時,施正文說道,以“實質課稅”來看待對賭協議的應稅金額更具有合理性。舉例來說,若對賭雙方采用正向對賭模式,當目標公司完成對賭目標時,投資方會對融資方進行業績補償,這部分價款同樣會課稅。他說道,目前我國稅法文件上對賭協議的稅務處理沒有特別安排。其實從民法角度來看,最高法已在《九民紀要》中對“對賭協議”的性質進行了初步界定,明確其為股轉交易的一部分,將股權轉讓與對賭協議看作為一個交易整體,這也構成了以“實質課稅”來計算應納稅額的民法依據。
施正文也強調,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是股權轉讓與對賭協議可以構成整體交易征稅的重要前提。所謂合理商業目的就是對賭協議首先要在民法上具有合法性,此外還應在稅法上不以避稅為主要目的。立法機關及司法機關可以通過對法律的解釋與補充,以應對多變商事交易中稅法的需求。
此外,本案二審法院也對稅收調整政策表達了期待。二審法院在裁判文書中寫道,為了營造更加規范有序、更顯法治公平的稅收營商環境,建議稅務部門積極調整相關政策,持續優化稅收征管服務舉措,為經濟新業態提供更合理更精準的稅收規則,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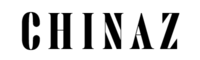








 滬ICP備2021030333號
滬ICP備2021030333號